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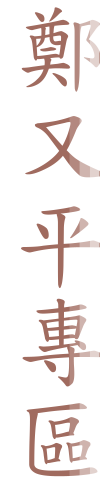 |
全球化與國際移民:國家安全角度的分析 |
||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財團法人賢德惜福教育基金會董事 |
||
一、全球化浪潮下有增無減的國際移民現象
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在人類歷史上已經有相當的歷史。大規模的國際移民、人口遷徙,可以追溯至西元前3世紀。早在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之前,就出現了遷移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migration),大批人口進行跨洋或跨洲的遷徙移動。如果我們聚焦在當代的國際移民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移民潮,初期是以OECD會員國為目的地之區域性、經濟性移民為主,這是由比較貧窮的西方國家遷徙到較為富裕的西方國家;1960年代以後,移民的接受國逐漸由西歐、北美、澳洲地區國家,移轉到東南亞、西非、南非、拉丁美洲,乃至於1970年代以後的中東地區國家。世界各國、各區域都深受國際移民的衝擊與影響。國際性人口遷移的歷史模式與型態不停的在變動,每一波移民潮的人口組成特質、移民的動機、誘因,乃至於移民所追求的就業機會也各有特色,不能一蓋而論。
換言之,國際移民是一個持續性的人類歷史現象,它不是違反歷史常規的特例。人口的移動,通常與人口成長、科技的進步、政治的衝突、戰爭、自然災害,甚至瘟疫都有密切的因果關聯。在近代史上,殖民帝國的現象,工業化的進程,與民族國家的興起,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成長,在這一些現象的發展過程當中,大規模的國際移民一直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但是由20世紀的後期乃至21世紀的今天,國際移民在全球化浪潮中所展現出來的社會、經濟、與政治意涵更是遠超過之前幾世紀中人口移動所產生的效應。各國的政治領導人,也開始高度重視國際移民的現象與各國政府的移民政策。國際移民不只是內政的議題,更早已轉變成外交與國際政治中的重大議題;它所影響的層面,由經濟的發展到社會福利到國家安全與區域性的穩定,幾乎無所不包。因此在後冷戰時期,國際秩序的建構過程中,國際移民早已成為一個全球化的議題與世界各國共同關切的焦點。
當代國際移民的特質就是它的全球化特性。因為國際移民直接影響到各個國家與區域的發展及穩定,它透過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各種過程,滲入並影響全球各地的社群、經濟體與政治社群。舉例來說,這些人口的流動往往會造成地主國就業結構的改變,經濟發展的波動,族群組成的多樣化,以及各個主權國家之間所產生的跨國性的連結。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相互依存」度的逐漸提昇,不僅拉近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各種互動關係,更使得不同社會與人民之間的交流互動愈來愈頻繁。除了經貿活動交流大增;資金流動也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場中打破了傳統國家行政彊域的藩籬;資訊化的社會也將國際間科技的交流轉換成網路上的家常便飯。
伴隨著這個高度相互依存的國際政經體系而來的還有一個影響深遠的現象,即就是大規模的跨國性人口移動遷徙。這種勞動力的跨國遷徙有其不可忽視的經濟、政治與社會效應。尤其是當移民成為定居者之後會使移民的接受國(receiving state)出現「多元族群社會」,而形成該國國內各族群之間能否融合相處的問題。
1980年代中葉以降,人口的遷移不只在數量與規模上快速成長,其性質與方向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我們可以預期的是,國際移民將會持續成長,而且將成為經濟全球化浪潮下,影響全球變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至於造成人口遷移與國際移民會持續成長的因素有下列幾項:
1.全球南北貧富差距持續惡化擴大,使更多的勞動力會以移民手段來追求改善生活條件。 2.部份國家內部人口成長壓力,生態環境壓力,政治發展趨勢,使得部份族群或勞動力企圖遷徙他鄉以逃避壓力。 3.後冷戰時期中國際局面及權力結構均勢重新調整,部分國家內部多元族群之間的衝突與暴力增加,可能導致大規模的難民現象。 4.國際經濟競爭日益激烈,保護主義浪潮方興未艾,新的貿易塊壘浮現,也會帶動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遷移。 5.全球生產體系的結構重整,深化了工業先進國與開發中國家落差,吸引勞動力的遷徙。[1]
國際移民或人口遷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商品的國際貿易與資本的跨國流動通常會帶動人口的移動。而全球化浪潮下,各國之間文化的交流,運輸交通的便捷,媒體的蓬勃發展等因素都會直接/間接地促成國際移民的出現。
如果我們檢視各個民主國家的憲法,我們不難發現,人民有遷徙的自由是一個普遍被接受的原則。而移民可以分為 "移居進入一個國家"與 "移出一個國家"的兩個層次。雖然主權國家的憲法通常會保證人民有遷徙的自由,但是政治現實顯示,各國政府的政策,對於本國的移民或外籍勞工、外籍的新郎新娘、甚至於國際難民或追求政治庇護者,都有相當嚴格的管制政策與審核門檻。國家機器在國際移民的議題上所展現出來的強制性與自主性,與政治號召之中所標榜的自由、人權,是有一定程度的矛盾。儘管各國政府移民政策的框架與規範有增無減,由20世紀中葉以降,趨勢也逐漸緊縮,但是國際移民的現象依然在平穩的成長。
本文嘗試回顧檢討政治學領域中處理國際移民的相關理論,並從兩大類研究分析途徑中,探討國家(state)在國際移民的範疇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分析國家基於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的因素,如何看待國際移民的現象;以及各國政府面對全球化的浪潮時,如何在"國家安全"及 "相互依存"兩者之間求取平衡點。此外,本文也將說明自由主義全球化理論的論證尚不足以解釋民族國家所面對的「全球移民危機」及國際移民對國家安全的威脅。要完整解析國際移民現象,勢必將人口移動視為獨立變項 (independent variable),而非傳統社會學/經濟學解釋中的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將國際移民現象化約為單純的經濟利益與成本效益的邏輯推導,是嚴重的錯誤。國際移民的政治與政策分析,不能忽略掉各國的文化、歷史、信仰、價值觀與國家認同。在制定移民政策的過程中,國家主權與認同的考量,經常會超越特定企業團體、產業部門、社會階級的個別利益。
二、國際移民對主權國家的挑戰
正當各國費心構思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新秩序該如何安排時,跨國性的移民與人口遷徙早已巧然躍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核心舞台。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統計,在1993年估計國際移民人數高達一億,其中西歐有一仟伍佰萬,美國有二仟萬、澳洲、加拿大吸收了八佰萬,國際難民人數則攀高到一仟玖佰萬之眾。(UNPF,1993) 到了2000,在出生國以外地區生活的人數,已經高達一億七千五百萬人。而這些官方統計數字還不包括非法移民部份。
國際難民的大量湧現,早已成為各國政府手中的棘手問題,歐洲的巴黎、波昂、維也納、布魯賽爾等大城市中充斥了大量來自巴爾幹島、東歐、乃至第三世界的難民,非法移民、外勞,以及這些外勞在當地出生的子女。許多政府還得費神因應國內激進的排外壓力與反外勞移民的極右派政黨。兩德統一後,德國政府發現由前東德蜂擁湧入前西德地區的經濟型難民壓力實在難以承擔。法國政府則是深怕阿爾及利亞的回教基本教義派的狂熱造成太多的難民逃向巴黎。在美國[2]華府的國會山莊上,中國、古巴、海地的政治難民及政治庇護問題變成壓力團體說客的熱門話題;美國加州、佛羅里達州的州長競選過程中,候選人則是急於辯論是否應該限制或取消移民的雙語教學;禁止使用西班牙、中文或韓文招牌的權利,甚至徹底防堵非法外來移民進入州界。由美國到英國、法國,勞工團體紛紛向政府施壓要求禁止外勞輸入,防堵非法移民,以免當地勞工的就業機會與工資水平受到侵害。旅日的大批韓僑則是日本政府與韓國政府之間的歷史恩怨糾葛要素之一,而這批旅日韓僑也正是海外援助北韓政府的重要地下資金管道。以色列在美國的主要支持者是美國的猶太團體;北愛爾蘭共和軍在美國的說客則是愛爾蘭裔美人。
國際移民並非先進工業國的專有問題。並列開發中國家之林的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政府設有專責機構處理外勞輸出事宜,負責與外勞輸入國政府相關部門交涉談判。這些東南亞外勞每年寄回母國數以千萬美金計的僑匯(remittance),這些僑匯正是這些開發中國家改善國際收支平衡的主要抑注來源。巴基斯坦政府擔心的則是如何處理來自阿富汗的難民;南非政府擔心的不只是來自鄰近非洲國家的非法移民與走私客,議會還慎重考慮是否要實施高級技術人才本土化的政策。埃及政府對聯合國經濟制裁利比亞憂心忡忡,因為利比亞可能將數以萬計的埃及外勞遣送回國,這對埃及早已疲弱蕭條的經濟更會是一大打擊,而且還可能使埃及境內回教基本教義派狂熱團體興起。
冷戰結束後,蘇聯解體、東歐共產家紛紛解組、分裂,許多國家的邊界管制形同虛設,造成大量人口遷徙以尋求政治上的自由或經濟上的改善。東歐國家的族群衝突、宗教迫害、也造成了大量的政治難民逃往西歐地區。吾人可以發現國際移民的影響與衝擊是多層面的、跨國際的,更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國際政治經濟議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無一能夠倖免。在當代的全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國際移民不僅是主權國家一個迫切的政策議題,更是一股推動國際政治經濟變遷的力量。
三、國際移民的類型
要分析國際移民的政治效應,就必須先瞭解移民的類型與發展階段。大體上,國際移民有下列五種[3]:
(1) 經濟型移民
這是比例最高的移民類型,大多數移民是到另一國家去追求就業機會或是改善生活水準。經濟型移民有可能只是暫時性,但也不乏最終成為永久居留的移民。只要世界各地存在經濟發展程度差異,平均國民所得有相當落差,社會福利制度良窳不同,經濟景氣的差別,都可能會造成持續不斷的人口移動現象。第三世界的低經濟成長率並不一定會使當地人口外移,以美國、西歐、與中東產由油國經驗來分析,經濟型移民多數仍是需求導向 – 因為地主國勞力短缺而引發。也有先進國家對第三世界人口壓力可能造成的「人口傾銷」政策(Population Dumping Policy)表示憂慮,但並沒有證據顯示移民比率與人口成長率成正比。[4]
另外有一種高級白領階級的移民現象值得一提。這種人口移動數量不大,多數因為是與多國籍企業的海外投資或是經貿交流機會有關,例如在一九九二年統計數字顯示日本人在亞洲區有85000人客居亞洲其他國家,而其中有34000人是受雇於日本企業。英國在1999就核發了45000張工作許可證給外籍的專業技術人士。[5][6]
(2) 國際難民與政治型難民
難民是一種非自願性移民,為了逃避戰亂、種族清洗、政治迫害、內戰、甚至環境污染災害。其中環保型難民更是近年來因為生態保育意識高漲,全球生態環境的惡化(如聖嬰現象與溫室效應)等因素才使學者發現此種類型移民的趨勢。當然,也有一部分是為了追求更理想的政治自由環境而自願移民。
因為戰亂而生的難民潮仍然是此類型的主要來源。依照聯合國難民高級委員會(UNHCR)的資料顯示,前南斯拉夫的分裂造成一九九一年有近六十九萬南斯拉夫難民紛紛流亡到其他歐洲國家。國際難民總數在1976年是280萬,1980年有820萬,1985年突增為1160萬,到1993年已經是1890萬人。[7]
(3) 家庭團聚(依親)型移民
其於人道因素,多數國家都會允許獲得永久居留的移民的家人或親屬入境依親團聚。所以這類移民是其他各類移民的衍生結果,往往會形成連鎖式的移民現象。[8]
(4) 非法移民
對多數先進富裕國家而言,非法移民是日益嚴重的燙手政治問題。對多數國家而言,也會造成選舉上的爭議,因為已經定居的少數族群移民團體往往會組成遊說團體對移入國的國會施予壓力,要求放寬管制或就地合法化等安排,而政治人物為了吸引少數族群的選票也會予以考慮。另一方面,因為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漲,而使得許多先進工業國家的社會中也出現了排外現象,尤其是對非法移民的防堵及管制也不乏當地民眾的支持。非法移民對地主國社會福利及公共建設會造成負擔,也多少影響到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與工資水準。
有學者估計台灣的非法移民至少廿萬人,日本有卅萬人、澳洲可能高達十五萬人,而馬來西亞的非法移民可能高達七十萬人,美國將近有三佰萬之眾。歐洲的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也都有嚴重的非法移民問題。如何妥善處理已經在境內的非法外來移民實在是各國政府一項重大考驗。
(5) 身份轉換的移民
二次大戰後因為國際之間交通便利,經貿及文化交流頻繁,不只提昇了各國之間相互依存的程度,更因為觀光、求學、受訓、訪問、交流等因素,而出現了大量的短期人口遷移。這些人有一部分會在入境後轉而尋求政治庇護、或以婚姻、依親等理由申請改變身份,進而成為外勞或永久居留的移民。
四、國際移民的階段發展模式
雖然國際移民有不同的類型性質、起源,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情境下也會出現不同型態,學者Castles與Miller將各國經驗綜合後提出下列的經濟型國際移民四階段模式:
第一階段:年青(男性)勞工暫時性移民,他們通常有設定賺取僑匯以改善母國的家族生活或追求一定的個人儲蓄的目標,希望存夠錢之後就衣錦榮歸。
第二階段:經過一段時間,一部份外勞返回母國,另有一部份或因當地生活品質較佳、收入良好,或因儲蓄目標仍無法達成,決定延長居留,在地主國逐漸依血緣、地緣而發展出移民自身的社交互助網絡,甚至結婚生子。
第三階段:許多外勞移民開始安排申請家庭成員依親重聚,開始有長期居留的心理準備,逐漸強化對移民地主國的認同。族群社區漸漸出現,並發展出移民族群的各種社會團體、宗教團體等機制。
第四階段:永久居留,但是因地主國政府政策或當地居民的接納程度不同,有些可以被社會主流接納、融合、合法居留或歸化;有部份移民則是在政治上受到排斥,在社會經濟地位上成為邊緣人,而終於形成固定的少數族群。[9]
這種移民的階段發展模式特別適用於(1)殖民地居民移往原殖民宗主國; (2) 地中海國家移往西歐、澳洲;與(3) 亞洲、拉丁美洲國家移往北美洲的移民型態。較不適用於國際難民或具有專門技術的移民。
五、國際移民的經濟學/社會學解釋與政治解釋
在政治學範疇裡,無論是比較政治、公共行政與國際關係領域,長期以來都沒有對國際移民這個主題有過多的著墨。從知識史的發展過程當中看來,政治學者對於國際移民議題的關切,直到1980年代以後才得到廣泛的重視。正因如此,傳統的移民理論,對於國際移民的現象所提出來的解釋理論架構往往是偏向經濟學或社會學的解釋。其中,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與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就是由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所引伸出來的解釋;移民網絡(migration network)與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則是與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有密切關聯的社會學解釋。直到1980年代與1990年代,我們才開始看到國際移民的研究領域,在政治學範疇內逐步成熟,而國際移民的政治學(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才開始被普遍的接受為一個值得重視的政治科學研究主題。在這一波的研究工作裡,我們也看到了將 "國家機器"作為重要政治解釋獨立變項的各種論述。 "Bring the State Back In"不只在比較政治中開花結果,更在國際移民的研究領域中產生重要的影響。[10][11]
在政治學的領域裡,我們要如何解釋像國際移民如此重要的議題為何長久以來被學界忽視? 這就得由政治學的發展過程中去回顧了。從二次大戰以後到冷戰結束之前,國際關係的政治學者,通常將政治領域分為兩纇,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與低階政治(low politics)。尤其是現實主義的觀點認為 "高階政治"才是國際關係最重要的研究課題;所謂高階政治包含軍事問題、核武議題、國家安全、外交政策,乃至於戰爭與和平的研究。相較之下,低階政治所關切的各種社會與經濟議題,如經貿、人口、環保、移民之類的主題,相對上就沒有得到政治學界足夠的注意。但是由70年代末期美蘇的低盪(détente)階段之後,新的國際關係議題開始浮上檯面,從世界各國經貿交流的激增,到多國籍企業(MNC)與海外直接投資(FDI)的興起,各類的全球經貿議題吸引了一批原來屬於傳統國際關係領域的學者,如Robert Gilpin、Joseph Nye、Peter Katzenstein、Myron Weiner、Nazli Choucri、Robert Keohane、Stephen Krasner、Richard Samuels等主流政治學者的注意,將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關注範圍,開始由安全(security)的領域擴張到了經貿領域。當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與教學再度成為顯學,國際政治經濟學(IPE)這一個新興的領域也在1980年代以後蔚然成形,而「國際移民」此一領域也在1990年代之後伴隨著環保議題、人權議題、海外援助、科技移轉、產業競爭力、恐怖主義議題等,一併進入政治學界的注意焦點範圍。國際關係的學者在研究了國際之間的人口移動,以及族群和民族主義的問題後,發現國際移民對於民族國家的主權與國家安全的確會產生不可忽視的效應。
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領域裡面,對於國際移民現象的解釋大體上有兩大學派,第一種是
A、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理論(globalization theory):
這類學派認為隨著國際經貿交流的成長與國家之間相互依存度的提升,民族國家的主權與管制力量,已經被各類跨國性力量逐步侵蝕。民族國家的主權有衰微的跡象與式微的趨勢,從商品的生產國際化,貿易的全球化,資本市場的全球化,到國際勞動力市場的人力交流,每一股力量都把世界從過去的高度堡壘化的民族國家,逐漸推向一個 "去領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階段,人為的國家疆界已經被全球化浪潮裡的各種經濟力、文化力、與社會力,一步一步的解構。[12]
在全球化的跨國經濟發展下,我們看到了跨國性的社群的出現,越來越多的白領勞工甚至藍領勞工必須跨越疆界,去尋找更高的工資,或者更佳的就業機會。這種現象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之間尤其明顯,例如:美國與墨西哥,美國與加拿大,歐盟各會員國之間的人口流動。不僅如此,許多跨國性的移民網絡,也分別在移民的地主國與母國之間發展出來。這種移民網絡強烈影響早期移民的親友後續的移動。研究顯示,移民的第一手資料往往來自於已經移民到目的國的親友,這類跨國聯繫的網絡,也有助於移民在新的社區裡安家立業。對於全球化經濟環境裡的許多企業來說,國際移民是一個值得充分利用的高度經濟效率的管道。
全球化的經濟浪潮創造了一個有利於國際移民的環境。首先,勞動市場交易成本的降低,交通網絡的發達,與通訊科技網絡的發展,都使得各國政府的移民管制政策無法完全發揮作用。各國的企業與政府面對日益白熱化的國際產業競爭,幾乎別無選擇,只有朝著開放、解禁、自由化的道路前進。而這種趨勢在勞動力市場及資本市場中尤其明顯。另一方面,1970年代以後開發中國家的債務危機,使這些國家必須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性調整政策的嚴苛要求,而這一種情境也間接的鼓勵更多窮困國家的人民轉進富裕國家。最典型的例證便是1990年代中葉的墨西哥,它在財政危機爆發之後,披索貶值,連帶出現了90年代下半期由墨西哥遷徙到美國的人口大幅成長。
主張全球化觀點的學者強調,國際移民與歐洲的經濟成長及整合是同步成長的,所謂的客籍勞工(guest workers)與外來移民,會帶來足夠的經濟利益,並駁斥所謂 "勞動力總合的謬誤",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內的就業機會總數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外來移民與本地勞動力之間並非零合的互動關係。他們認為民族國家的觀念已經過時,無法充分掌握世界經濟體系的快速變遷。
基本上,這個學派的觀點與世界體系理論的結構性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基本上它們都認為國際移民是源自於國際經濟的二元性(duality) ,只要國際經濟分工體系裡存在著二元性,就會有誘因與壓力存在,讓個別勞動者跨越國界,追尋更好的就業機會。問題是這種流動最後會不會達到「柏瑞圖最適境界」(Pareto optimality),仍然是一個無解的爭議。也有學者認為,國際移民只會將國際經濟分工體系的二元性與各國勞動力市場裡的二元性進一步惡化;他們認為資本主義體系是依靠著一個龐大的產業後備軍,持續供應低廉的勞動力,來克服資本累積過程裡不斷會出現的危機。
總之,全球化學派強調當國際移民的網絡日益發達,跨國聯繫的社群逐步發展,移民的數量會持續增加。隨著經濟的景氣循環的波動,各個經濟體對外來移民勞動力的需求雖然會出現各種起落,但這種對外來勞動力的需求,在先進的工業國家裡,是一種 "結構性的鑲嵌"(structural embeddedness)。換言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要長期持續的成長發展,就不能缺少一批廉價、順服的外籍勞工。
全球化的理論會強調民族國家企圖管控國際移民的努力終將徒勞無功。這些民族國家的國家機器至多僅能夠透過國家的政策作為,去延緩或者扭曲商品、勞務、資金、與勞動力的全球化市場發展。它們最終還是無法旋乾轉坤。如果國家機器企圖在全球化的環境裡運用公權力,去嚴格管制邊界,限制人民的出入境,或者立法限制外來移民的工作權、生存權等各種公民權益,恐怕也是事倍功半。以德國為例,德國有關移民及公民歸化的嚴苛法規,也無法避免德國今日成為歐洲最大的移民接受國。
國際移民的全球化學派,將政治因素與國家機器的角色邊緣化,本質上這一類的解釋變成一種 "非政治化"的邏輯,強調國際貿易與國際移民兩者基本上深受國際經濟分工體系的影響。在這種邏輯下,對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國家主權、或公民權益的討論都變成次要的枝節。
全球化學派的理論盲點在於它們完全忽視了國際移民的政治解釋,他們把重心完全放在社會與經濟層面。在這類的理論思維中,國家機器的公權力與管制,幾乎沒有任何的解釋空間。國際移民的現象,在他們眼中完全是由社會經濟的變數來決定。
然而,國際移民與人口移動終究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現象,它更是一個政治問題。雖然自由主義經濟學者會主張國際勞動力市場機制的運作應該尊循市場法則。在政治現實中,卻沒有任何政府會對移民採取「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政策,多數的政府是扮演主導的強力干涉角色。
B、新現實主義的政治性解釋:
另外有一纇研究途徑強調政治性的解釋變項(political variables),則是認為國家機器作為一個理性的主權行為者,面對國際移民的現象,它必須堅持內部政治穩定(political stability)與外部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的考量。或許國際移民能產生多種經濟效益,但是它也可能造成國際之間的衝突以及國內政治上的緊張對立。 因此,在現實主義理論觀點的眼中,國家身處無政府狀態(anarchy)的國際社會,面對日益成長的國際移民現象會有一種國家安全的兩難處境(security dilemma),它們被迫要盡可能保障自己國家的主權,並且尋求強化國家權力與管制能力的各種方案。在此一學派眼中,國際移民或者是國際難民,都會衝擊到國家安全,所以國家機器是否開放接納或者管制排斥國際移民的政策決定,都必須以國家利益為考量的依歸。所謂的『國家利益』指的就是任何政策作為能否強化國家權力,提高國家的國際地位。[13]
另一方面,部分西方先進國家認為非白種人的移民大量湧入,有可能造成對自身文化認同的威脅,甚至扭曲既有的國家認同,進一步威脅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穩定性。支持這類觀點的學者基本上認同一個假設:任何一個社會吸納外來移民的容量是有限度的。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稱之為『容忍的門檻』(threshold of tolerance) 。許多西歐政府認為,仇外情緒的滋長與大量的外籍移民是息息相關的,因此政府的管制是必要之惡。例如,美國政府為了防止大量難民潮的侵入,進而主動干預海地的內政;或者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在1990年代主動介入巴爾幹半島的政治紛爭,也是基於類似的動機。
另有一群學者將他們的注意焦點轉移到支持或反對國際移民的政策聯盟(policy coalition)。除了文化與意識形態因素外,還有經濟利益因素可以影響到社會內部各種支持開放政策的利益結盟,對於基本公民權益,社會福利權益,或者是投票權的保障理念,也有助於這種政策聯盟的形成。
國際移民可以改變一個社會的族群成分,影響政治勢力的分布,影響政黨的選票結構,甚至於微妙的改變了公民的國家認同。因為大量的外來移民,加上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有利於支持開放性移民政策的政治勢力興起。當外籍移民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裡能夠有法定的權利保障,進而立足深耕,一旦外籍移民與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孫能夠獲得公民的權益保障[14],這些少數族群就自然能夠影響地主國的國家政策及選舉政治。[15]
不僅是政客會去追求外來移民的選票支持,高度依賴外籍勞工的企業界也會加入遊說的行列,支持開放性的移民政策。隨著國際產業結構的變化,今天所謂的外籍勞工,不只是非技術性的藍領低階勞工,也包括了知識密集與科技密集產業的高階白領勞工。19世紀以降的西歐國家歷史經驗中,就充滿了企業遊說政府支持進口勞工的案例。這種經驗在現階段台灣的產業界也有類似情況出現,這些企業會強調,切斷他們的外籍勞工或專業技術人士的供應來源,就等於是對其進口原物料課以高額關稅一樣有殺傷力。但是有研究顯示,當移民問題一但牽扯到國家認同因素時,市場經濟利益考量未必能佔上風。當國家主權、邊界管制的政策議題被簡化成國家認同的爭議時,移民政策的開放或封鎖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邏輯問題,而是一個牽連到文化、意識型態、道德價值的複雜政治化(politicized)問題了。[16]
支持自由貿易與支持開放性的移民政策兩種利益團體的動機是有所區別的;通常支持自由貿易的團體往往是基於經濟利益,而支持開放性移民政策的聯盟則是帶有更多的意識形態、文化、與法律的色彩。對於移民政策的論證,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理念往往會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決定各個團體支持或者反對移民政策的鬆緊。也有一些國家內部的移民政策辯論,會聚焦在人權與公民權的辯論上。總的來說,強調人權與市場經濟利益的聯盟(Rights-Markets Coalition),會傾向支持開放性的移民政策。反之,對於國家認同、族群因素等變項的重視,往往會使移民政策趨向於緊縮。
當然,政治性解釋的弱點在於過度強調政治決定論,以至於無法充分解釋後[17]冷戰時期有增無減的國際移民現象。
國際移民現象經常會因為政府及其他各種政治勢力,基於非經濟性的原因,強迫,鼓勵、或者阻撓人口的遷徙。一個政府或許可以在國防上保國衛鄉,但是歷史經驗顯示,許多國家根本無法有效遏止非法移民偷渡入境以尋找就業機會或是其他福利。非法移民的氾濫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現象,人蛇偷渡組織早已變成是國際化的犯罪集團,而非法移民的持續存在與成長,又更進一步的讓各國政府感受到對國家主權的威脅;這種焦慮也使大家強烈感受到對移民與邊界管制的政策需求。
對移民地主國政府而言,移民政策的考量重點通常不是在於是否要開放或禁止移民的「二選一」選擇題,而是在衡量1)移民的數額多少及品質、資格的限制;2)移民在國內經濟體系內應該發揮的功能、扮演的角色;3) 要求移民同化於主流文化中,還是尊重其各自語言、文化的差異性;4) 長期目標是鼓勵移民返回母國落葉歸根,或是協助他們永久居留在地主國;5) 對移民在當地出生的的子女與家族依親團聚的要求如何處理。對許多輸入外勞的國家而言,政府不僅有把關及管理的責任,更試圖要將外勞來源多元化並嚴格禁止其長期居留,以免造成依賴與政治上的少數族群問題。[18]
政治性解釋學派中,有一批新自由主義者(neo-liberals)則是強調制度變項的重要性。他們與新現實主義者(neo-realists)都強調國家的理性抉擇,以及利益因素的重要性;但是,新自由主義者與新現實主義者不同之處在於,前者認為國家利益的概念應該被分解為各種社會、經濟團體相互競爭,影響國家決策的總合結果。所以,他們認為各種社會、經濟、與政治行為者的利益與偏好,必須要明確的釐定。透過這種分析途徑,就可以解釋國家在移民政策上所作的政策選擇,究竟是源自哪些因素。新自由主義的研究途徑巧妙的結合了國內與國際政治因素的分析。
另一方面,以Robert Keohane 為代表人物的一批學者,則是以國際制度因素為主要變項來分析國際政治經濟現象。其它如Robert Gilpin所提出的霸權穩定論,強調在美國經濟霸權開始式微之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要找出如何在沒有霸權的情況下維持世界市場的秩序,解決國際合作的問題。Keohane等學者認為答案在於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以及國際制度典範(international regimes)的建構。所以GATT、IMF、WTO等等,都是他們理念上認同的解決方案。問題是,在國際移民的領域中,除了大規模的國際難民問題以外,大多數國家都尚未感受到多邊國際合作的迫切性。而在國際難民的議題方面,也只有聯合國難民高級委員會(UNHCR)曾經發揮過有限度的影響力。一直到1990年代以後,OECD的會員國家才開始感受到管控難民潮的急迫性。
六、國際移民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新現實主義者強調國家在全球化的環境中依然面對各種國家安全的威脅,國際移民就是無法避免的安全威脅之一。國際移民可以對國家安全造成下列五項威脅:
一、 國際難民與國際移民如果是反對或敵視母國的政權,會造成母國與地主國之間的緊張關係: 在國際關係史上,如果地主國對於移民母國的大批政治異議份子給予政治 庇護或居留權,往往會造成母國與地主國之間的敵對關係。例如1990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美國對於中國大陸民運份子提供政治庇護,就被中國視為對其內政的干預。此外,布希總統對於中國大陸留學美國學生簽證的延期,也被視為是一種不友善的行為。有許多政治性的難民是因為恐懼母國政府的迫害而流亡海外尋求庇護,民主的國家會提供居留權,讓他們有機會能夠提供資訊與金錢以支持母國內的反對勢力。民主國家的人道考量不一定會被移民的母國視為友善的措施,1970年代美國政府准許伊朗的巴勒維到美國就醫,引發了伊朗基本教義派強烈的反彈,最後導致美國大使館的人質危機。[19]
有一些接受難民的國家,會私下資助難民團體進行反政府的工作。著名的案例就是美國對反卡斯楚政權異議份子的援助,以及對尼加拉瓜流亡政府的支持;印度政府也曾經提供武器給孟加拉的自由鬥士以抵抗巴基斯坦的軍事政權;沙烏地阿拉伯與美國則曾經支持過阿富汗難民對前蘇聯軍隊進行游擊戰。換言之,國際衝突可能創造國際難民,但是國際難民也可能製造國際之間的衝突。
相當數量的國際難民也可能形成『飄零族群』(diaspora)現象,早期有猶太人,愛爾蘭人,巴勒斯坦人,近有錫克人、車臣人。它們在民族屬性上與文化上具有跨國界的特性,成員會認同自己的母國或早已滅亡的故國。[20]飄零族群現象不一定是源自於難民,原本是純粹經濟性的移民也可能會因為政治態度與信念的改變,轉而敵視母國政府。譬如威權時代的南韓與台灣都有相當數量的移民在美國組成反對威權的民主運動團體;伊朗的柯梅尼在掌權之前,也曾經流亡法國領導伊朗的飄零族群團體。母國的威權政權也有可能會運用情治人員到移民國去監視這些反對團體的行動,甚至會採取激烈的手段去破壞反政府團體。台灣民主化之前,國民黨政府與海外台獨團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就是一個明顯案例。所以「飄零族群」團體經常會成為地主國與母國之間的政治爭議。
二、國際難民可能會對地主國造成政治風險: 阿拉伯國家對巴勒斯坦難民組織的支持,不僅是提供了反以色列政治勢力的資源,也在他們自己國內培養出一群強而有力的特殊政治團體。PLO的政治能量一度甚至足以影響阿拉伯國家的內政與外交政策。科威特政府就曾經驅逐過巴勒斯坦難民,因為他們認為巴勒斯坦難民已經威脅到科威特的國家安全。1990年波斯灣戰爭中,沙烏地阿拉伯政府也曾經將近百萬的葉門人驅逐出境,只因為葉門人支持伊拉克的海珊政權。
北愛爾蘭、巴勒斯坦、錫克、庫德族群都曾經被懷疑在他們所居住的地主國發動過恐怖主義攻擊,非法走私軍械及毒品,甚至參與反地主國的政治活動。所以不少國家對於國際難民團體都會產生疑慮,這種疑慮有些時候可能被過度誇張,但是在國際恐怖主義活動日益猖狂的世界中,特別對於中東難民的安全疑慮似乎是一個難以消除的現象。
三、國際移民可能會對地主國的國家/文化認同形成威脅: 傳統的移民理論假設國際移民進入地主國之後,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同化進入當地社會的文化主流。這種看法通常假設移民會在一到兩個世代的時間裡徹底的同化。隨著移民被主流的政治、社會、文化生活方式吸納,移民原有的族群認同可能會逐漸消滅於無形。採取同化觀點的論者認為說,對少數族群的保障配額或雙語教育的政策只會惡化族群的對立,拖延濡化的過程。有人認為地主國的經濟景氣好壞,失業率的高低,都可能影響到當地民眾對於外籍移民的接納程度。
從19世紀末的美國就已經有了反對開放歐洲移民的聲浪,到了21世紀之交,英美各國的新法西斯與新納粹主義運動依然層出不窮。究其原因,就是因為大規模的外籍移民引發了人們對於族群純度與國家認同遭到威脅的疑慮。移民的地主國通常會傾向於接納具有類似語言、宗教、文化與族群背景的外來移民。此外,移民數量的多少也會影響到判定認同危機是否存在的因素。當一個社會必須面對大規模的非法移民,而這些移民又不具有類似的文化或者國家認同意識,地主國社會往往會產生嚴重焦慮感。由菲律賓與印尼非法進入馬來西亞的移民就曾經引發當地政府的疑慮。在這種國家認同或文化認同的危機意識下,外來的國際移民不論其經濟效益多少,反而會激發仇外的心態及反對文化多元主義的聲浪。本土意識的強化會造成反移民的政治勢力集結,而地主國的政府在此情況下常會緊縮移民政策。這種反移民勢力主要是源自於主流族群社會中的邊緣份子,他們會要政府採取行動,解決外來移民遲遲無法同化融合的問題。[21]
當然,多元文化主義的模式在澳大利亞、瑞典、加拿大都有相當程度的成功。這些多元文化社會都願意接受文化的異質性,以及國際移民的引入所帶來的社會變遷。在這些社會中,移民不會被強迫順從或接納主流的文化或語言,他們可以依其意願繼續維持固有的語言、文化、生活方式。採取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會認為移民是對主流文化的豐富而非威脅。相對於文化多元主義的社會,美、法兩國則是堅持對外來移民採取同化整合的傳統做法。這種國家認為透過公民歸化的政治整合,可以為社會及文化的整合提供先決條件。它們認為針對外籍移民所設計的文化與社會政策,反而可能鼓勵與主流社會隔離的少數族群聚居現象。所以,美國的模式主要是依賴私領域(private sphere)的整合力量,透過家庭、社區、宗教團體等等,來同化吸納外來移民。遺憾的是,美國的少數族群至今未能充分融入所謂的美國社會主流,而法國的族群衝突更是方興未艾。值得注意的是,各國經驗顯示,外來移民適應與整合的過程需要時間與包容,徹底的同化至少需要好幾個世代的時間才可能完成。
Samuel Huntington分析1965年之後大量外來移民造成對美國的國家認同的挑戰,甚至已經威脅到美國社會、政治的制度與傳統。他分析世界各國回應此一威脅的辦法不外乎: 1. 限制移民,包括限制人數,提高核准入境的標準,例如要求專業技能、教育水平、特定來源地,或者只允許移民停留有限時間。 2. 對移民採取消極政策,不強調同化整合。當文化背景不同的外籍移民人數眾多時,就可能產生移民聚居的社區,任其自成一體,相對隔絕於主流社會。 3. 接受大量移民,促進整合同化,讓移民融入地主國的社會和文化。
Huntington分析美國的外來移民浪潮對國家認同的衝擊,提出了令人憂心的四種前景:未來的美國可能是下列幾種可能性的混合體,首先,美國可能失去核心文化,成為多元文化社會,但繼續保持忠於『美國信念』的原則,此原則為美國的團結提供意識形態的基礎。其次,他認為1965年之後,大量拉美裔移民的湧入,可能使美國分成兩種語言,兩種文化,進一步惡化原有的黑白對立現象,甚至可能在美國內部出現「西語系的魁北克」。第三,核心的美國文化和美國信念遭到挑戰後,可能促使白人排斥、驅逐、壓制其他族群與文化。這是一度居於統治地位的族群面對外來族群團體的崛起對自己形成威脅時,所可能採取的反應措施。但是美國也可能走向Huntington所支持的第四種選項,就是引導少數的宗教、族群團體恪守「盎格魯─新教文化」,新教價值觀,說英語,保持歐洲文化傳統,忠於『美國信念』的原則。[22]
四、國際移民可能造成對地主國經濟與社會的沉重負擔: 雖然外來移民可能有解決勞動力短缺等各種經濟效益,但是異族的文化習慣甚至於犯罪行為,都可能造成社會上的集體焦慮,侵入地主國的國際移民或多或少都會對社會福利資源形成壓力,此外居住、教育、衛生、醫療種種資源成本,也可能造成當地人民的反彈。
如果地主國懷疑母國政府有意的在推動人口傾銷政策,將母國社會中的劣質或不受歡迎份子,包括罪犯、少數族群等有以的外銷到地主國,那麼地主國的政府與人民就可能不願意承擔國際移民所帶來的各種相關的社會成本。這種案例在1960年代美國與古巴的案例中明顯可見,印度與巴基斯坦在70年代也產生過類似爭議。[23]
五、高素質的國際移民對於母國的經濟安全可能形成的衝擊: 以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兩岸關係為例,大量的資金與技術投注中國與大量的白領技術性勞工甚至於高階的工程師,外流到中國大陸的產業部門,被視為是對於母國的國際競爭力的打擊,進而威脅到台灣的經濟安全。[24] 開發中國家的高級技術人才流失給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也是一個令領導菁英頭痛的問題。[25]
一般而言,雖然多數學者強調合法移民對先進工業國家的經濟效應是正面積極居多,但是轉回頭來分析移民對移出國的影響,多數人則是著重在負面的效應。決定外移的移民並不是批評的焦點,而是移民的事實對國內經濟、社會及社區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左派學者認為這種由第三世界向核心工業國家的人口外流是一種「不平等交換」,是「世界資本體系」的結構性質之一,造成國際所得分配不均,深化邊陲國家對核心國家的依賴附庸,惡化國內技術人才外流,進而造成文化認同的迷失。[26] 七、結論
综上所述,國際移民的現象是民族國家無法避免的政治現實,國際移民不僅是全球化經濟體系內的必然存在的一種現象,它也是民族國家所面對的眾多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來源之一。國際移民不只是一個經濟議題、外交議題,更是一個國家安全議題。所有的政府,在制定國際移民政策的時候都必須面對國際體系的結構性限制條件,以及國內各種政治因素的影響。換言之,國際移民的政治分析,應該同時在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兩個層面進行;全球化過程中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整合的力量,加上區域性經濟合作的趨勢,使得民族國家的主權不斷的受到挑戰。排他性的國家忠誠與國家認同,在移民全球化的時代裡,也逐漸遭到質疑。所有國家都面臨了國家認同與公民權在政治與文化層面上重新定義的問題。[27]
可以肯定的是,在全球化浪潮下,國際移民的趨勢將不會淡化或消失,而民族國家的影響力及國家認同的政治角色也不至於在近期內銳減,世界各國都必須準備接受更豐富的文化異質組合與更多元化的人口族群組合。在宏觀的歷史潮流裡,全球化所牽動的不只是人口的遷徙,還有商品經貿的交流、科技知識的移轉、金融資本的流通等等。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效率如何兼顧公平正義,經濟全球化如何與國家主權及國家安全取得平衡,以避免全球化的弊端,這些問題都還有待政治學界進一步的研究。 [1] James H. Mittelman,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8-73 [2] Peter Stalker, Stalker's Guide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ttp://pstalker.com/migration/index.htm [3] 移民的分類有多種主張,Stalker (2002)就將其劃分為: 屯墾移民(settlers)、契約勞動移民 (contract workers)、專門技術移民 (professionals)、沒有身分的勞動移民 (undocumented workers)、難民和庇護申請者 (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等五類。 [4] Myron Weiner, "International Emmigration: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ssess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Between Poor and Rich Countries, October 6-8, 1983 [5] Peter Stalker,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xford, UK: New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02) [7] UNHCR Statistics, 1994 [8] Peter Stalker,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xford, UK: New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2002) [9] Stephen Castles and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 in the Modern World (NY: The Guilford Press, 1993) [10] Caroline B. Brettell &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NY: Routledge, 2000) [11] 有關這方面理論發展,可參見 Theda Skocpol,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State Power and Societ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 Kenichi Ohmae, The Borderless World (London: Collins, 1990); Kenichi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NY: Free Press, 1995) [13] Myron Weiner, The Global Migration Crisis: Challenge to States and to Human Rights, (NY: Harper Collins, 1995) ; Myron Weiner 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ecurity, (CO: Westview Press, 1993) [14] 有關移民的公民權、社會權等權益之演進,請參考 James F. Hollifield, "Ideas, Institutions and Civil Society: On the Limits of Immigration Control in Liberal Democracies" IMIS-Beitrage 10 (January, 1999); 及Michael Bommes and Andrew Geddes, eds., Migr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Contemporary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00) [15] 周育仁、鄭又平,政治經濟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8): pp. 397-424 [16] 參見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NY: Routledge, 2000) [17] 參見Donald J. Puchala et al. eds., Immigration into Western Societies: Problems and Policies (London: Pinter, 1997) [18] 周育仁、鄭又平,政治經濟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8): pp. 397-424
[19] 參見Myron Weiner, The Global Migration Crisis: Challenge to States and to Human Rights, (NY: Harper Collins, 1995) ; Myron Weiner 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Security, (CO: Westview Press, 1993) [20] 參見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Y: Simon & Schuster, 2004): Ch.10 [21] 參見Caroline B. Brettell and James F. Hollifield eds., Migration Theory: Talking Across Disciplines, (NY: Routledge, 2000) [22]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Y: Simon & Schuster, 2004) Huntington將他在《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點的視角,由國際轉向美國國內;他分析了當前美國的國家認同所面對的挑戰,認為美國已經面對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他反對世界主義式與帝國主義式的解決方案,強調捍衛發揚「盎格魯─新教文化」的根本特質,以避免美國國家面對分化衰落的危機。他主張要保持並加強美國自立國以來的獨具素質。
[23] 有關兩岸之間的技術人力流動,參見Tse-Kang Le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T Talent Flow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e Taipei/Shanghai/Silicon Valley Triangle", Asian Survey 42(2), 2002: pp.230-250 [25] 有關專業技術人力的遷徙,參見Robyn Iredale, "Migration Policies for the Highly Skilled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4 (3), Autumn 2000 [26] W. R. Böhning,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4); Mary M. Kritz, Charles B. Keely, and Silvano M. Tomasi eds., Global Trends in Migr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NY: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1981) [27]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David Goldblatt,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NY: Polity Press, 1999)
|
||
| --2006-08-16-- | ||
|
|
||
| 。版權所有 (c) 2006 財團法人賢德惜福教育基金會。 Copyright 2006 (c) S.D.S.F.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
||
| 管理登入 | ||